資本熱捧的人工智能,為何在金融領域四處碰壁?
來源: http://www.iheima.com/zixun/2017/0307/161719.shtml
資本熱捧的人工智能,為何在金融領域四處碰壁?
 一本財經
一本財經

做2B生意,就不要指望“一飛沖天”,行業要沈下心,專心技術和模型。
本文由一本財經(微信ID: yibencaijing)授權i黑馬發布,作者墨菲。
去年的AlphaGo,今年的Libratus,“人工智能”的風潮在各行業湧動。
金融領域也不例外,“智能投顧”成為金融科技的新寵兒。
去年開始,傳統金融機構入局,資本熱情異常,智投行業一片欣欣向榮,不乏重塑行業、誕生獨角獸的野心。
如果智能投顧有一個“形象”,它應該是一個穩健、溫和的機器人,它沒有“摧枯拉朽”的力量,它倡導“健康理性”,也無法做到“永勝不敗”。
被“保本保息,剛性兌付”等慣壞的網貸投資人,在股市中“習慣投機,急速獲利”的用戶,他們是否會喜歡這個機器人?
01 強勢崛起
12月6日,招行在深圳有個小發布會,卻沒料到,在行業內掀起了軒然大波。
旋即,在招行新上線的APP5.0中,出現了一個叫“摩羯智投”的藍色標識,它是招行推出的智能投顧產品。
為什麽叫摩羯?
“摩羯星座,代表的精神是智慧、穩重、嚴謹、紀律”,招商銀行回應了網友的疑惑,“這些正是投資理財所要具備的要素”。
藍色的摩羯小機器人的誕生,對於智能投顧行業來說,是一個不容忽視的“信號”。
此前,智能投顧只是創業公司的戰場,大家都在“摸索突圍”階段,在質疑中蹣跚。
“大家之前甚至疑惑,這是不是一群人小打小鬧、創造了一個偽概念”,璇璣CEO鄭毓棟認為,“只有行業大佬進入智能投顧這個行業,才說明這個行業大有可為”。
“智能投顧”的風潮,在中國最大的商業銀行入場後,瞬間被推向頂峰。
實際上,“智能投顧”火熱的背後,是整個“人工智能”技術的集中爆發。
2016年3月,機器人AlphaGo大勝李世石,人類一敗塗地;今年,AlphaGo化身“master”重出江湖,連續60局無一敗績;另一人工智能Libratus,在大河賭場贏得德撲勝利,斬獲20萬美元獎金。
人機對弈的失敗,像只蝴蝶,輕輕扇動翅膀,攪動了行業對智能的憧憬和“將被取代”的恐慌。
“未來十年,出現最多的獨角獸公司,肯定是人工智能公司”,創新工場CEO李開複在演講中說道。
人工智能會首先落地在“數據最大、最快能產生價值的領域”,李開複認為,“比如說,金融領域的銀行、保險、券商、智能投顧、AI量化基金”。

而人工智能在金融的運用,最先冒尖的,就是“智能投顧”。
所謂智能投顧,就是機器人投顧,取代的是以前“投資顧問”的角色。
“對於人工智能的興起,我們是既興奮又恐慌”,漣漪資本創始人夏翌稱,整個投資行業,對人工智能的心情是複雜的。
機器取代了個人“投資顧問”的角色,未來是否會取代專業投資機構的“投資經理人”?
在種種複雜的心情下,資本對人工智能變得極度熱情。
國外美國智能投顧代表Wealthfront,目前已獲得了12.9億美元融資;國內,彌財、財鯨、理財魔方、藍海智投等早期智能投顧項目,也獲得了千萬級融資。
據知名管理咨詢公司科爾尼預測,到 2020 年,智能理財市場規模將突破 2.2 萬億。
資本的火熱和傳統金融機構的入局,市場一片欣欣向榮。
而行業的現狀,真的一帆風順嗎?
02 獲客之難
在行業發展初期,業內人士認為,國內智能投顧發展面臨三大難題:監管、模型和用戶。
去年證監會曾強調,“發現互聯網平臺未經註冊、以智能投顧等名義擅自開展公募證券投資基金銷售活動的,將依法予以查處”。
實際上,監管不是針對“智能投顧”,而是打擊沒有牌照的機構,頂著“智能投顧”的名義,代銷基金。
年末,招行摩羯的出現,再次表明了監管的態度,有牌照資質的機構,安心探索;沒有牌照的,就安心研究技術,別亂碰銷售。
另一方面,智能投顧通過一年多的摸索,基本已解決數據模型的問題。
之前外界普遍認為,因缺乏行業大數據,中國又是“政策市”,導致模型很難確立。
“但實際上,市場的數據和產品的數據都是非常標準化的”,璇璣CEO鄭毓棟解釋,“雖然某一個基金產品可能是近幾年才出現的,但整個市場,比如美股市場、A股市場、黃金市場,這些數據都是特別久的,足夠搭建算法模型”。
因為中國的國情特殊,不是所有的數據都適用,需要一定的清洗。
互金行業專家顧崇倫表示,“一些極端的數據,諸如2006股改前、黑天鵝事件等,這些數據,不適合放在通用模型中”。
也就是說,數據並不缺,剔除極端數據後,已足夠搭建模型。
解決了監管、模型問題之後,行業現在最難突破的,是獲客等生存問題。
“很多平臺運營了一段時間後,發現獲客很難,即便註冊後,智能投顧表現不穩定後,用戶就馬上流失”,某智能投顧平臺負責人稱,這一流失,就是永久性流失。
“獲客,才是智能投顧面臨的最大挑戰”,顧崇倫表示,“直到現在,依然是創業公司最大的軟肋”。
這實在不能怪智能投顧,中國的投資用戶的心理,實在算不得“健康”。
國內用戶投資偏好兩極分化嚴重:一種是賭徒心理,喜歡刺激的“追漲殺跌”,信奉“短期翻倍”,以炒股的散戶為主要代表。
另一部分,是“絕對保守”、“風險厭惡”用戶,他們習慣把錢存在銀行,或嘗試一些相對安全的貨幣基金。
對於這兩類用戶,智能投顧這個小機器人不太“討喜”。
“智能投顧的優勢,在於長期穩健的分散投資,是一個控制風險波動的產品”,鄭毓棟稱,短期投資,智能投顧的優勢並不能展現,“以璇璣為例,去年來看它的收益不能算高,短期還有些小幅的虧損”。
也就是說,智能投顧擅長的是“長期投資”,而非“短期投機”。
激進的用戶,瞧不上智能投顧的收益;保守的用戶又擔心資金的“保本”問題。
在網貸行業爆發後,中國還產生了一批新的“理財用戶”。
“最開始,P2P平臺就是以高息迅速網羅一批種子用戶”,顧崇倫表示,但這種簡單粗暴的獲客方式,顯然不適合溫吞的智能投顧平臺。
《華爾街見聞》曾挑選了一些代表性平臺,以中等風險為標準,對比了不同智能投顧平臺去年下半年收益表現:

(圖片來源:華爾街見聞)
一波波的降息潮後,P2P網貸平臺已告別了動輒年化20%以上的高息,網貸行業平均綜合利率已經降為9.68%(網貸之家數據)。
對比來看,溫柔的智能投顧,利率對他們也沒有太多誘惑力。
這就是行業現狀,智能投顧的表現,尚沒有攪動用戶熱情,反應平平。
市場的冷清和資本的火熱,形成了鮮明對比——它依然要面對很多中國式難題,關乎人心,關乎心態,關乎投資理念,這恐怕都無法短期內解決。
03 零和遊戲
行業將何去何從?從美國智能投顧市場中,我們可以找到某種軌跡。
花旗銀行報告顯示,從2012年到2015年底,美國智能投顧管理的資產規模幾乎從0增加到了190億美元,發展非常快。
最新數據顯示,截止2016年底,Wealthfront資產管理規模超過40億美元。
但Wealthfront發展並非一帆風順,也曾多次更新發展方向:Wealthfront前身,想做股票方向的社交平臺,但美國散戶炒股人群並不多;舉行的“虛擬投資”大賽,投資人也並不踴躍。
美國尚且如此,火熱表象的背後,行業發展也是冷靜而盤桓不定的。
“別神話了智能投顧”,顧崇倫認為,行業對人工智能的期待值過高,“因為人工智能要追求大概率的獲勝,必要爭取安全的前提上,去搏最大的‘浮動收益’”。
直接的結果就是,智能投顧最好的表現,也是中等偏上,在收益上不會特別突出。
“智能投顧面對的是大眾,不可能有一個策略是讓所有的大眾都賺取了超額收益”,鄭毓棟解釋,“有超額收益必有負超額收益,誰能來給你貢獻負超額收益?”
從短期來看,“投機”的本質就是“零和遊戲”,一方的收益,意味著另一方的損失。
所有的超額收益就是一個固定大小的水池,當舀水的人越來越多,每個人或得的水就越來越少。
這也是為何,任何一個新的投資模型,總是在剛進場時迅速套利,一旦湧入的大量玩家,平分的收益就變少。
這決定著,智能投顧這個機器人,是溫和的,別期望它帶來一夜暴富的力量。

盡管行業掣肘很深,但智能投顧領域,依然有兩個突圍方向。
一股,是“招行摩羯”為代表的傳統金融2C模式。
傳統機構手中,C端客戶充沛,掌握著中國大部分財富。
以招行為例,數據顯示,招商銀行管理著中國最有價值的中高端個人客戶的金融總資產達5.4萬億,理財資產管理規模達2.3萬億,金融資產托管規模為9.4萬億。
更為關鍵的是,傳統金融用戶保守,原本的銀行利率本不高,智能投顧的表現,對他們來說,已算“驚艷”。
另一股,轉場2B,成為技術、產品的服務商,“慢慢發展”。
璇璣在去年就提出了B端戰略;藍海智投在去年8月獲得Pre-A輪融資投資時,也宣布2B的智投雲。
實際上,去年很多卡在“獲客”關卡的平臺,開始悄悄謀劃2B的轉型之路。
“這是一種迂回的解決方式”,顧崇倫認為,2B模式,暫時不需要考慮獲客和市場培育問題,打磨模型,積累用戶數據,在市場教育成熟後,再挖掘C端用戶。
但做2B生意,就不要指望“一飛沖天”,行業要沈下心,專心技術和模型。
一年多的探索後,玩家們發現,“智能投顧”這個溫和的機器人,暫時沒有攪動風雲的野心與力量。
與“投機”對抗,和“剛性兌付”戰鬥,這個小機器人,需要戰勝的,是中國式的投資難題,還有人心貪欲……
[本文由一本財經(微信ID: yibencaijing)授權i黑馬發布,作者墨菲。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,不代表i黑馬立場。推薦關註i黑馬訂閱號(ID:iheima)。]
人工智能
贊(...)
分享到:

D&G創辦人四處點火頭 曾推「奴隸涼鞋」 揶揄#Me Too
1 :
GS(14)@2018-11-25 11:12:37https://www.mpfinance.com/fin/da ... 2455&issue=20181125
【明報專訊】意大利奢侈服裝品牌Dolce & Gabbana(D&G)近日因一段指導亞裔模特兒以「小棍子」(筷子)進食「偉大的」意大利薄餅的宣傳片,被質疑貶低中國文化,之後有網民在Instagram提出質詢,卻與品牌創辦人之一Stefano Gabbana的ins帳號展開罵戰,Gabbana辱罵「中國是屎一樣的國家」,令事件升級。D&G之後聲稱相關帳號被盜,上述言論與Gabbana無關,但未能取信於內地網民。D&G兩名創辦人上周五在微博官方帳號用普通話說「對不起」,欲平息風波。事實上D&G以往的張揚作風,已為他們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爭議。
《華盛頓郵報》時尚評論專家Robin Givhan曾形容,兩名創辦人Domenico Dolce和Stefano Gabbana發表了政治不正確意見,最多也只會聳聳肩,毫不在乎。Gabbana曾這樣說:「我喜歡自由。自由,自由,自由,自由。我喜歡說出我的想法。我不怕。我所說的不會錯,只是超出社會規範。但這真的是我的想法。」
D&G的品牌創作,以至兩名創辦人的言行,經常冒天不之大不韙。2007年該公司推出的一輯廣告,展示一名穿泳裝的女模特兒被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按在地上,由一堆赤膊男子圍觀,被指有強烈的輪姦暗示。廣告其後在意大利等地被禁或抽起,D&G公司當時批評監管落後,把創作和真實行為混為一談。
「輪姦暗示」廣告 意大利被禁
D&G在2013年的春季系列,在裙子上印上blackamoor風格的北非女子,又展示了一系列以黑人女性頭像為設計的耳環,被指令人聯想到美國奴隸制,質疑品牌以奴隸文化賺錢。除了販賣奴隸衣服、奴隸耳環的爭議,D&G在2016年推出的一款名為「奴隸涼鞋」(slave sandals)的女裝涼鞋,也受到外界非議。
兩名品牌創作人的言論也一樣惹火。2015年,Dolce向意大利《Panorama》 雜誌炮轟試管嬰兒是「化學的、合成的孩子」。他認為同性戀者不應製造試管嬰,言論觸怒了育有試管嬰的Elton John,他直接發動粉絲抵制D&G。Gabbana反罵Elton John是法西斯分子。除此以外,Gabbana也曾批評Lady Gaga有肚腩,形容美國樂壇小天后Selena Gomez醜,又批評超模Kate Moss穿的Valentino服裝不好看,到處點着火頭。
成梅拉尼婭衣櫥大牌
近年Gabbana曾質疑 #MeToo全球反性侵運動誇大了性侵的出現率,又堅稱性騷擾在意大利並非問題。他說:「所有關於美國女性的事情,我們都沒有相同的東西,因為我們非常尊重女性。我們的心態完全不同。」
他形容部分問題是你請我願。Gabbana說:「這不是新鮮事。(意大利名導演)維斯康提(Luchino Visconti)向(奧地利男演員)漢密保加(Helmut Berger)和阿倫狄龍提出上牀……但聽着,這是由你決定的。這是真的。大家都知道。 20年後你說:『啊!他摸我屁股!這不是暴力。』」
當很多知名品牌都不願跟美國總統特朗普家族扯上關係, Tom Ford、Marc Jacobs等品牌更表明不會贊助第一夫人梅拉尼婭(Melania)服裝,D&G卻成為她衣櫥的大牌。當梅拉尼婭穿上D&G服裝出席公開場合,Gabbana就會上Instagram讚美一番,被Givhan形容他是梅拉尼婭的「單人啦啦隊」。這行為也令D&G在社交媒體成為針對對象。為此Dolce和Gabbana生產了印有#Boycott Dolce & Gabbana字樣的T恤回應,與反對者繼續互懟。
海港城店禁港人攝影惹抗議
較為港人熟悉的D&G爭議,是2013年初D&G位於海港城的門店禁止香港人在店外的行人路攝影,但內地遊客卻獲准拍照,觸發大量群眾聚集在該店外攝影,以示抗議。
資料來源:華盛頓郵報、glamour.com
明報記者 黃展翹
[企業地球村]
2 :
GS(14)@2018-11-25 11:12:49https://www.mpfinance.com/fin/da ... 4093&issue=20181125
【明報專訊】D&G是一家全球知名的時裝公司,由意大利設計師Domenico Dolce和Stefano Gabbana創辦,兩人的姓氏也是品牌名稱的來源;總部位於意大利米蘭。D&G曾經為麥當娜、蒙妮卡·貝露琪、濱崎步、伊莎貝拉·羅塞里尼、吉賽兒·邦臣和凱莉·米洛等名人設計服裝。
社交媒體上多次掀起的杯葛D&G運動,對D&G品牌的影響不得而知。截至今年3月底的12個月內,其收入按年大致持平,錄得12.9億歐元(約125億港元,以3月底匯率計算)。但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按年跌7.1%至1.56億歐元(約15億港元,以3月底匯率計算)。
去年收入125億港元
《華盛頓郵報》時尚評論專家Robin Givhan形容,D&G的設計是為富人之中的富人而設。
今年4月D&G品牌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打造了一場金碧輝煌、花團錦簇的時裝秀,展示猶如童話世界式的華衣美服。不惜工本為貴客打造夢幻的舞台,被行業觀察家質疑了一下成本。Dolce當時這樣回應:「對不起,這是你的錢嗎?不是,好的。」
時裝秀展示的Alta moda(高級時裝),動輒價格數萬美元,但未必是一般情况下可以穿著的。Givhan形容,穿這些衣服的場合,可能是在俄羅斯財閥或中東皇室的超級遊艇,又或在保安森嚴的歐洲莊園。
對於有評論認為這品牌的衣服開價貴,Dolce反駁:「你會問米開朗基羅的作品多少錢嗎?你不要問價格。美是不可以錢來衡量的。」
兩創辦人曾是情侶關係
60歲的Dolce與56歲的Gabbana認識30多年。Dolce是西西里島一名裁縫的兒子,Gabbana是平面設計師。兩人於1985年創立自己的時裝品牌。有一段時間,他們是情侶關係。這種關係在2005年結束,但他們的商業伙伴關係持續。當歐洲其他設計師將自己的品牌賣給大型企業,每隔幾年換一次創意總監。他們仍是D&G的掌舵人。這品牌最近關閉了以T恤和牛仔褲為主的較低價業務,專注滿足少數富人的品味。
[企業地球村]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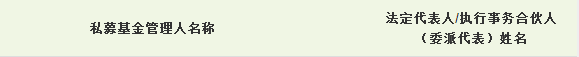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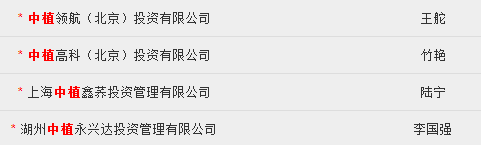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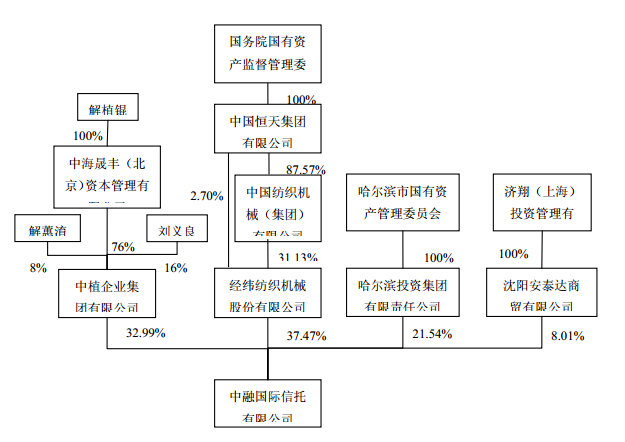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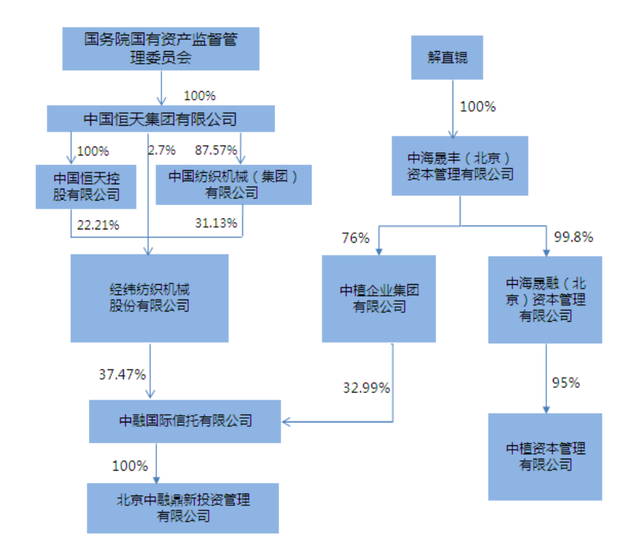








 匿名用戶
匿名用戶